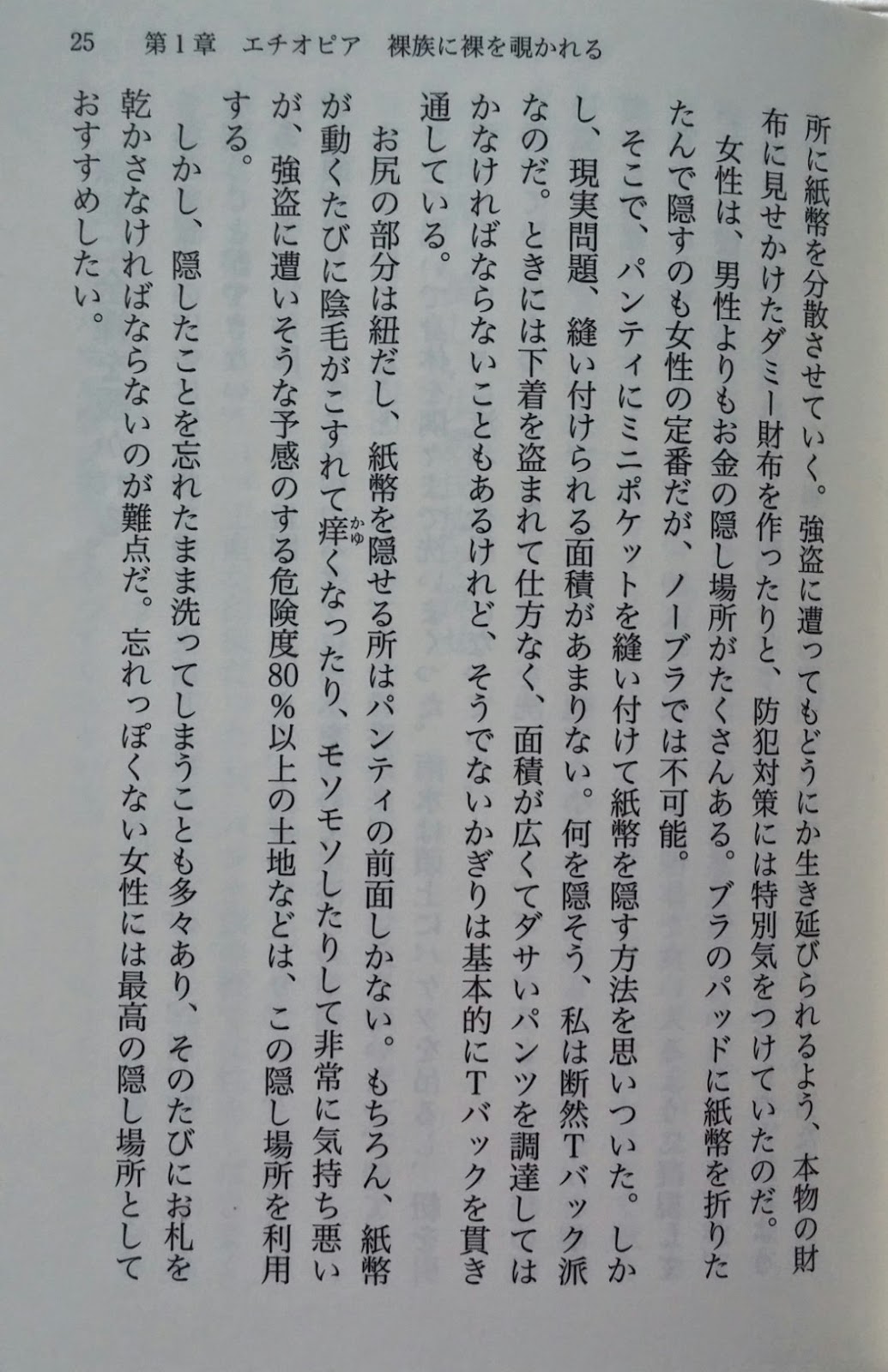序 我踏上旅途的原委
「刺激無法傳達至心室,造成心律不整。目前還不會影響日常生活,但日後症狀如果惡化,可能得裝心律調節器。一勞永逸的治療方法……沒有。」
剛進高中沒多久的十五歲春天,醫生的話讓我懷疑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。雖然在健康檢查時發現我的心臟可能有毛病,進而接受精密檢查,但我實在萬萬沒想到將來或許得裝心律調節器……。
當時的我沒有興趣、沒有夢想、不用功、也沒參加社團,只是無所事事的過日子。
可是醫生的驚人之語,瞬間驚醒我這個毫無幹勁的少女。
「接下來,我要找出能讓我投注熱情的事物,努力過每一天。不走他人安排好的人生,而是邁向自己決定的人生!」
我有生來首次為過去糜爛的生活後悔。
不過,人生目標不是說找就找得到,我就這麼懵懵懂懂地過著高中生活。
在入學典禮結束後為新生舉辦的社團介紹中,有個社團引起我的注意--是啦啦隊社。我很訝異這世上竟然有女孩跳舞時眼睛閃著光彩、笑得如此開懷。我有預感投身啦啦隊可以稍稍改善我內向的性格,也相信啦啦隊可以補足我當時欠缺的(熬過痛苦的)耐力和活潑的笑容。
馬上加入社團的我,早上五點起來到速食店打工、白天上課、晚上練習啦啦隊,每天雖然累得要命,沒空休息或玩樂,卻自然湧現活著的充實感。
後來有天,我們啦啦隊在全國賽奪冠,並受邀參加在佛羅里達州舉辦的世界盃國際啦啦隊錦標賽,我也以選手的身分同行。生來第一次的海外旅行令人興奮。現在回想起來,「初次出國」是一切的開端。
佛羅里達的景物在我眼裡顯得閃閃發亮,然而我最驚訝的是絕大多數不穿胸罩的女性。她們晃著胸部,傲然走在街上的模樣,在我眼底象徵著自由。我在國外感受到日本沒有的自由。
我追求的「事物」正是這個。
我下定決心,要飛向寬廣的世界!所以回日本後,為了能夠常出國,我做了各式各樣的努力和準備。從上課、社團活動和打工中擠出一點時間出國旅遊。
就這樣,愈來愈愛旅行、又對世界各國深感興趣的我,決定由只需念二年的短期大學,轉到要念四年的大學研修歷史。甚至為了替旅途留下更美好的記錄,跑去上攝影學校。然後,在畢業的同時選擇到美國留學。
不是長期的世界旅行,而是留學,否則父母不會同意。
然而在抵達美國後,我才知道身上的一百五十萬圓根本不夠付大學的學費。
沒有摸清留學的費用就跑到美國,聽來或許愚蠢,卻也很像我會做的事。
既然如此,乾脆用這一百五十萬圓挑戰環遊世界──我繞著地球跑的漫長旅程便從此開始。
我先遊北美,讓自己適應海外生活後,再轉戰歐洲。但在義大利途中,我的錢全被偷走,不得已只好回國。而後我去了大洋洲,並在出發滿一年時重回日本,工作存錢一小段期間,才又到亞洲、中東、非洲和南美,幾乎環遊世界一周。
交通方面,如果是板塊相連的國家,我都盡可能搭乘長途巴士,如果是跨海的國家則利用飛機移動。沒有路線和時間的限制,真的是自由旅行。我耗費二年的時間跑遍全世界。
一切全從第一次出國,在不穿胸罩的女性身上感受到的自由氣息開始。現在想想,我渴望翻轉以往的生活和價值觀就是從那一刻起。
我在日本的時候,總在意他人的眼光。做出和其他人一樣的打扮、思考,無法跳出框框外的生活簡直叫人喘不過氣來。
我不希望回顧僅此一次的人生時後悔!才踏上「丟掉胸罩」的個人旅程。
本書介紹我造訪的五大陸九十個國家裡,印象特別深刻的二十一個國家所發生的小故事。
對日常生活感到窒息的女性朋友,請務必脫下胸罩再來讀這本書。我相信這麼做能讓妳不出遊,也能享受「自由」。
衣索比亞
遭裸體部族一窺胴體
激烈的椅子爭奪戰
抵達東非衣索比亞首都˙阿迪斯阿貝巴的我,在天還未亮的凌晨四點,進入戰鬥模式。
在晨霧中前往巴士總站後,我見到許多衣索比亞人,虎視眈眈地等著搭上目標的巴士。沒錯,衣索比亞的長途巴士是由壯烈的椅子爭奪戰開始,所以這裡可說是戰場。
因為這裡有車票,卻沒有指定的座位,只能靠力量先搶先贏,在車門打開時就定位起跑!「準備~衝啊!」所有人背著行囊直往前衝!
不是我在吹牛,我國小到高中的一百公尺短跑成績常是學年冠軍,對短跑相當有自信。絕不能輸。
可是衣索比亞人身體的彈力不是蓋的。他們不斷超越我、輕鬆爬上巴士的貨架,然後手腳敏捷地綁好行李。
「吼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~!怎麼能輸給他們!」
我背著包包不服輸地死命狂奔,再笨手笨腳地爬上貨架,用繩子把背包固定住,接著衝上巴士,進行擠擠樂往裡面去。
巴士還沒發動,可你推我擠的車內已不斷左右搖晃。說什麼都得搶到座位才行。
在衣索比亞的長途巴士上沒有座位,不是日本滿員電車[1]沒有座位能相比的。聽說在路不平的衣索比亞搶不到位置,人包准受傷,因為身體會不受控制彈來彈去。
心急的我使出最後的手段──學相撲推開衣索比亞人,順利在椅子爭奪戰中獲勝!這下多少降低受傷的危險。
然而這只不過是序幕。巴士開始行駛時,車內也因為崎嶇的路面大幅度的左右搖晃,我頓時暈得一塌糊塗。
過沒多久,車子開上坑坑窪窪的路面,以致車體開始劇烈地上下彈跳。咚--嗯、咚──嗯!每彈一下,乘客的頭就毫不留情地撞上天花板。我想長時間在這種狀態下搭車,等到目的地時,我的小命也沒了。於是我試著觀察身旁的衣索比亞人,看有沒有什麼秘招。
結果大致分成兩種類型:在車子彈起時任憑腦袋接受撞擊的「石」頭,和配合晃動控制身體的賢者。
前者的頭蓋骨似乎異常堅硬,沒辦法當作參考。後者看來是抓準車子彈起來的時機,在座位上壓低身體。
我趕緊依樣畫葫蘆,卻抓不到訣竅,遲遲找不出壓低身體的時機。萬一不小心睡著的話,可能等我醒來時我的腦神經鍵已經全毀,也可能頭蓋骨破裂、與世長辭……。
除此之外,還有一件事困擾著我。衣索比亞人很少洗頭,其中有許多部族以紅土固定頭髮維持數個月,所以非常臭。這種強烈的氣味讓人忍不住想打開窗戶,可是衣索比亞人相信惡靈會從打開的窗戶入侵,而絕不開窗。
每當我快吐出來,想打開窗戶時,他們便會拚命阻止。不顧我得時時刻刻保護頭部,也不顧我得頻頻忍住作嘔的感覺,巴士只是一個勁兒地前進。
生命的價值砍到一〇四圓
衣索比亞的交通工具不只巴士,隨著旅程推進而有愈多機會改搭共乘的貨車。這種沒有車篷的貨車車斗上常擠沙丁魚,當地人根本站著在顛簸的道路乘車前進。
而且同車的除了人類,還有撲通撲通下蛋的母雞、隨地拉個不停的牛等家畜,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。整車的惡臭讓人直想拿棉花塞鼻子。
突然間,貨車急煞。開在我們前方的巴士,因渡橋攔腰斷裂跟著摔落河裡。「發生大事了」,我們車上的當地人魚貫下車。
我望向河川,心想這麼嚴重的事故,就算出現死者也是正常的,可是眼前的景象讓我忍不住懷疑自己的眼睛──沒人受傷,反而全生龍活虎的渡河!巴士都東凹一塊西凹一塊了,人卻毫髮無傷,這是什麼道理?
據我詢問當地人得到的解答是「他們在事故發生的當兒,打開窗戶逃了出來」。衣索比亞人的反射神經實在不容小覷!
在橋坍塌後,貨車無法再往開前。現在沒了渡橋,我若想過河,只能選擇自力救濟拔腿涉水。
當我背起包包、把褲腳盡可能捲向褲襠,準備踏進河裡時,當地人悄悄在我耳邊說:
「妳要小心,這條河裡有大鱷魚。」
咦!我指著河,問那些來事故現場看熱鬧的當地人。
「Crocodile(鱷魚)?」
當地人爭相回答。
「Yes(對)!Crocodile River(鱷魚川)。」
爸爸、媽媽,女兒不孝。你們含辛茹苦的拉拔我到這年紀,女兒卻可能淪為鱷魚的盤中飧。但我已經不能回頭了,只有祈禱不被鱷魚發現。我把心一橫,步入河裡。
河水濁得看不到有什麼生物潛藏在其中。以我的身高,水剛好淹到我的褲襠,所以褲子變得濕漉漉又沾滿淤泥。
比預期湍急的水流使我邁不開步伐,遲遲無法照我的意思前進。背包沉甸甸地壓在我的肩頭,身體隨時可能失去平衡,被河沖走。依現在的情況,什麼時候被鱷魚吃掉都不足為奇……。
當我繼續提心吊膽地渡河時,全身驟然變輕。其中一名在河岸看熱鬧的當地人,涉水提起了我的背包。
「加油!快到了!」當地人伸手拉我。
所以我雖全身濕透,倒也平安過河。萬歲!我沒被鱷魚吃掉。我沉浸在存活下來的喜悅中。
之後,我向那位替我提背包、並伸手拉我的好心人道謝。結果他伸長了手、咧嘴笑說:「十比爾。」比爾是衣索比亞的貨幣,當時十比爾約一百三十圓。以為他是熱心幫忙的我實在大受打擊。
但即使在這種時候,仍得殺價是窮背包客可悲的習性。金額最後砍到八比爾。
就這樣,我以一百〇四圓的代價成功穿越鱷魚川。
少數民族不可思議的結婚典禮
據聞衣索比亞約有八十個民族。要全數拜訪或許太強人所難,不過我希望盡可能走訪這些少數民族。當我秉持著這理念,繼續苦不堪言的遷移時,我發現了少數民族˙班納(Bana Tribe)的聚落。而且正巧遇上他們在舉辦傳統婚禮。
雖然長時間跋山涉水使我憔悴,但難得有機會目睹少數民族的婚禮,令我頓時打起精神觀禮。
突然「啪!」地一聲,劇痛傳遍我全身上下。班納族的男性竟毫不留情地鞭打我!咦?我做了什麼?難道外人不可以隨便觀禮嗎?
我忐忑的仔細觀察婚禮情形,沒想到應該是主角的新娘也被新郎鞭打得遍體鱗傷!怎麼能對女性下如此重手?我一時傻眼呆站著。
其實這是班納族傳統婚禮司空見慣的場景。聽說男性拿鞭子惡狠狠抽打女性是正統的儀式。既然是傳統,我也只能接受如此殘暴的禮節。除此之外,也有女性唱著嘶吼似的歌、男性行割禮等重口味的結婚儀式。為什麼要在這種大喜之日切除一部分的性器啊?
不斷遭鞭打的新娘,流著血吼叫著。我光看都覺得痛了,本人卻顯得很開心。眼神銳利的新郎則面不改色地揮鞭。
結果不是新娘、不是親戚,只是旁觀的我也蒙受其害,被男性們抽鞭子。明明精神和體力已因舟車勞頓透支,還慘遭鞭打,真的只能自嘲時運不濟。
一會兒後,少數民族的男性們停下手中的鞭子,當場跳了起來。蹦──!蹦──!不同於方才刑求似的儀式,現在有趣的Bull Jumping(跳牛)是屬於男性的傳統儀式。我也混在其中蹦蹦跳!雖然只是跳躍,但在先前精神和肉體持續遭到折磨的情況下,反倒覺得這是個輕鬆的儀式。我彷彿忘了旅途上的磨難,持續和班納族一起跳呀跳的。
女性私密的藏金庫
歷盡千辛萬苦把自己弄得疲憊不堪,好不容易抵達郡卡(Jinka)村,卻找不到可以過夜的旅舍。
就在這時候,我注意到紅色的十字標誌。看來是紅十字會的分支,他們在我上門詢問時,表示能提供我住宿的房間。
但來這的途中,被貨車司機們當肥羊宰的我,知道自己必須先將美金換成當地貨幣的比爾。
在這個不可能有ATM的村裡,換錢只能仰仗銀行。我根據當地人報的位置,來到看似銀行的建築物前,見到前所未有的景象。滿坑滿谷的鈔票不設防地疊在外面,甚至有些塞不進去滑了下來。在這間渾然沒有警備可言的銀行提心吊膽地換完錢後,我擔心回程有人尾隨,一路狂奔回投宿處。
而後將錢分別收在背包、褲子的內袋,還為了遇搶後仍能生活,特別準備了騙人的假錢包以防萬一。
女性能藏錢的地方比男性多。常有女性把紙鈔折好藏進胸墊,可是不穿內衣的人不適用這個方法。
所以我想到藏錢的辦法是為內褲縫上小口袋,只是現實上沒有我能縫口袋的空間。不瞞您說,我個人偏好丁字褲。除了有時內褲被偷,不得已換上醜陋的大內褲外,我一律穿丁字褲。
丁字褲的臀部是繩子,能藏紙鈔的地方只有前面。想當然耳,每當紙鈔移動摩過陰毛時會覺得癢,窸窸窣窣的很不舒服,可在這塊遇搶危險度百分之八十的土地,藏這裡最保險。
麻煩的是我常忘了錢藏在裡面,直接拿內褲去洗,還得晾乾鈔票。希望大家推薦對女性來說不容易忘又安全的藏錢地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