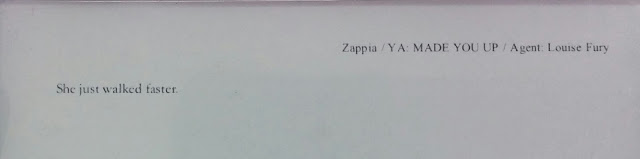序:解救龍蝦大作戰
如果我在雜貨店表現良好,我得到嗚呼。如果我表現優良,我可以看龍蝦。
今天我表現優良。
所以媽嘛放我一個人在主要走道中央的龍蝦槽前,自己去熟食區買爸拔愛吃的豬排。我很迷龍蝦。牠們的名字、蝦螯乃至鮮紅的色彩無一不吸引我。
我的頭髮也是鮮紅色,這種紅成立在人類以外的事物,因為人類的頭髮不該是紅色。橘色可行、赤褐色也沒問題。
但絕非龍蝦紅。
我抓著髮辮、貼上玻璃,與離我最近的龍蝦對望。
爸拔說我的頭髮是龍蝦紅,媽嘛說是共產黨紅。我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意思,但聽來不是好事。即使拿頭髮平貼在水槽的玻璃上,我仍不知道爸拔有沒有說對。我其實不希望爸拔或媽嘛說中。
「放我出去。」龍蝦說。
龍蝦動不動就要我放牠出來。我拿頭髮摩擦玻璃,當這水槽是住著精靈的神燈,而我的舉動會啟動魔法,然後我說不定能弄出那些龍蝦。牠們看來鬱鬱寡歡,一個搭著另一個擺動蝦鬚,蝦螯則慘遭橡皮圈捆在一起。
「妳要買嗎?」
藍眼開口前,我已在水槽玻璃看到他的倒影。一雙藍莓色的大眼──不對,那顏色太深了。海洋藍──過度偏綠。這藍色像我所有藍色蠟筆的融合。
我掛在脖子的嗚呼瓶子裡的吸管,從我唇邊溜開。
「妳要買嗎?」他又問。我搖頭。他推眼鏡,讓眼鏡回到臉上(他有金色的雀斑)正確的位置。這時,髒衣領滑落他的肩頭,他的肩上也有雀斑,可他身上附著池塘的浮垢和魚腥味。
「妳知道有螯龍蝦的化石紀錄可追溯至白堊紀嗎?」他提問。我搖頭(晚點得叫爸拔解釋「白堊紀」)後,大口吸嗚呼。
他一直看著我,沒看龍蝦。「節肢動物門軟甲綱十足目海螯蝦。」他說。
在唸到最後一個詞的時候,他的舌頭有些打結,但那無關緊要,反正我一個字也聽不懂。
「我喜歡科學分類。」他表示。
「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。」我說。
他又推眼鏡。「無患子目芸香科柑橘屬。」
「我還是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。」
「妳聞起來像檸檬。」
我感到心花怒放,因為他說「妳聞起來像檸檬」不是「妳的頭髮好紅」。
我知道我頭髮的顏色,任誰都看得出我的頭髮是紅的,但我不知道我的味道像水果。
「你聞起來像魚。」我告訴他。
他瑟縮,長著雀斑的臉頰燒紅。「我知道。」
我轉頭找媽嘛,她仍在熟食區排隊,短時間不會來接我。我抓住他的手。他嚇一跳、瞪著我們交握的手,像是剛發生了神奇但危險的事情。
「你要當我的朋友嗎?」我問。他抬頭重新調整眼鏡的位置。
「好啊。」
「要喝嗚呼嗎?」我遞出飲料。
「嗚呼是什麼?」
我怕他沒看到,將飲料推到他的面前。他接過瓶子、查看吸管。
「我媽說不能喝人家喝過的東西。不衛生。」
「可這是巧克力口味。」我回說。
他面帶難色看著嗚呼瓶、畏怯地吸了一小口後,推開瓶子,一時沒有任何動作、也不說話,但後來他彎下腰又喝了一口。
事實證明,藍眼不僅知道一大堆動植物的科學分類名詞,他根本無所不知。他知道超市每樣商品的價格(如果買下整個水槽的龍蝦,要價一百〇一點六八,稅外加)、每任總統的名字和他們就任的順序、羅馬皇帝──這特別讓我另眼相看。他知道地球周長為四萬公里,以及只有公的北美紅雀才是鮮紅色。
他真的認識不少字。
藍眼可以幫每樣事物找到一個詞。
比方說:併指畸形、地鳴、雨後的泥土味。這些字的意義像水溜過我的指縫間。
他說的話我大多不懂,但我不在意。他是我生來第一個朋友。第一個真實的朋友。
而且,我喜歡握著他的手。
「為什麼你有魚味?」我問他。我們信步繞著主要走道聊天。
「我剛在池塘裡。」他說。
「為什麼?」
「被丟進去的。」
「為什麼?」
他聳肩後,伸長手搔抓佈滿OK繃的雙腿。
「你為什麼受傷?」我問。
「環節動物門螞蟥。」
一串字溜出他的嘴裡像咒語後,他脹紅著臉、眼眶泛淚地狂抓猛搔。
當我們因此停在水槽邊時,超市店員從海鮮區的後方走出來,視我們於無物地打開龍蝦槽、留個縫,用戴著手套的那隻手撈出龍蝦先生,再關上龍蝦槽、拿龍蝦離開。
這一幕給了我靈感。
「你來這邊。」我拉著藍眼到水槽後面,看著他抹眼睛,直到他回視我。「你願意幫我弄出這些龍蝦嗎?」
他吸鼻子點頭。
我將嗚呼瓶放地上,平舉雙臂。「你可以抬高我嗎?」
他抱住我的腰、舉起我。我的頭一下子高過龍蝦槽、我的肩膀與滑動拉門同高。我是個小胖子,藍眼的腰就算承受不了我的體重斷掉也不奇怪,但他只是悶哼一聲、晃了兩下。
「穩住。」我告訴他。
滑動拉門的邊緣有把手。我抓著把手拉開門,裡面竄出的冷氣讓人直打哆嗦。
「妳要幹嘛?」藍眼問,他的聲音因使力和我的衣服顯得悶悶的。
「別吵!」我東張西望,目前沒人注意到我們。
龍蝦在拉門下方疊成一堆。我的手伸進水槽後,被冰水嚇了一大跳。我抓住離我最近的龍蝦。
我以為龍蝦會揮舞蝦螯、或擺動蝦尾,但牠沒這麼做。我像抱著沉重的貝殼離開水面。
「謝謝。」龍蝦說。
「不客氣。」我回答後,將龍蝦放至地面。
藍眼腳不穩地搖晃,卻沒鬆開我。龍蝦待在原地,一會兒才順著地磚爬行。
我伸手抓另一隻、又一隻、再一隻。很快地,水槽的龍蝦全在梅傑超市的地板爬行。我不知道牠們要往哪裡,可牠們似乎自有打算。藍眼喘吁吁地鬆手,我們因反作用力跌坐在一灘冰水。他看著我問:
「妳常做這種事情嗎?」他的眼鏡岌岌可危地扒著鼻頭。
「不常,」我說。「只有今天。」
他笑了。
這時,響起了尖叫聲。一雙手抓住我的手臂、拉我起來。媽嘛邊罵邊拉著我離開水槽。我越過她看到龍蝦已消失無蹤。冰水沿著我的手臂滴落。
藍眼仍站在水裡。他拾起我遺落的嗚呼瓶、揮手道別。我要媽嘛停下來,讓我回去問他的名字。
她反而加快腳步。
第一部:龍蝦槽
第一章
有時我覺得人們視現實為理所當然。
我的意思是你們可以分辨夢境和真實生活。雖然作夢時你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作夢,但你醒來馬上知道那不過是場夢,夢裡發生的事情(無論好壞)都不是真的。除非我們在演駭客任務,這世界是現實,你們大概只需知道這件事。
人們將此視為理所當然。
在超市命運之日過後的二年間,我一直相信我救了超市的龍蝦、牠們恢復自由爬回大海,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。到了我十歲那年,我媽發現我自認是龍蝦的救世主。
此外,她也發現所有龍蝦在我眼中都是鮮紅色。
於是她先澄清我並未釋放任何龍蝦。她厚著臉皮拉走我時,我的手仍未伸進水槽。接著她說明只有煮過的龍蝦是鮮紅色。我不相信她,因為在我看來龍蝦的顏色始終如一。她不曾提到藍眼,而我不需提問。我第一個朋友是幻覺:我躋身瘋子的第一筆輝煌記錄。
當我媽帶我看兒童心理治療師時,我首次確切瞭解精神異常的定義。
精神分裂症最快在青少年晚期顯現,但我年僅七歲便列入觀察、十三歲確診。一年後進一步被診斷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,因為我言語攻擊遞活動宣傳手冊給我的圖書館員,手冊內容是地下共產黨軍在公立圖書館地下室外活動(以圖書館員而言,她一直屬於可疑的類型──我不信戴橡膠手套遞書是正常且可信的行為,不管大家怎麼說)。
藥物治療偶有幫助。我知道是因為藥物生效時,世界不如以往色彩絢爛和有趣,比方說我看得出水槽裡的龍蝦不是鮮紅色、或覺得在食物裡翻找跟蹤器的行為很荒謬(但我還是照做,因為這麼做可以緩解我有如芒刺在背的偏執)。此外,當我的記憶模糊、感覺像是多天未眠、或試著反套鞋子時,我也知道藥生效了。
多半的時候,醫師根本不確定藥物造成的影響。「這藥應該能減輕偏執、妄想和幻覺,但我們得先觀察一陣子。對了,妳可能會感到疲倦。記得多喝水──這藥有可能造成脫水,甚至引起劇烈的體重變化。說實在,我們無法確定。」
雖然醫師很濟事,但我自行發展出一系列分辨虛實的套路:拍照。隨著時間過去,實像會留在相片裡,幻覺會淡去,而我從中發現腦袋偏好虛構的事物,譬如:廣告牌裡的人戴防毒面具,提醒行人德國納粹的毒氣瓦斯,仍是再真實不過的威脅。
我沒那個福分,將現實視為理所當然,但我也不會說我恨視現實為理所當然的人,因為那幾乎是所有人。我不恨他們。他們不是活在我的世界。
但這沒制止我渴望活在他們的世界。
第二章
高三、就學於東洲高中的開學前一晚,我坐在費尼根餐館的櫃臺後方,掃視窗外暗夜裡可疑的動靜。平時我的偏執症沒那麼嚴重,這要怪罪第一天帶來的壓力。被上一所學校退學是一回事,就讀新學校則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。整個暑期我在費尼根餐館努力遺忘這一切。
「妳知道如果費尼根在場,他肯定喊妳瘋子,再叫妳回去工作。」
我轉頭。塔克雙手插在圍裙口袋、靠著廚房大門,咧嘴而笑。他要不是東洲高中唯一的消息來源──及我僅有的朋友,我早破口大罵了。塔克是費尼根餐館的雜工、服務生兼出納,更是我認識最聰明的人。身材瘦長的他戴著眼鏡、油亮的黑髮總一絲不苟地往前梳。
他不知道我的事情,所以他說費尼根會喊我瘋子純屬巧合。當然費尼根知道我的病情,他姊姊(我目前的治療師)替我爭取到這份工作,可是員工──如葛司,我們寡言的菸槍廚師──都不知情,我打算保持現況。
「哈哈。」我試著耍酷。「壓下妳的瘋病,」我腦海裡的小聲音說:「別表現出來,妳這白痴。」
我同意接下這份工作只為呈現正常的一面,但或許多少也因我媽強迫我接下這份工作。
「有問題嗎?」塔克走過來、靠在櫃臺一邊問。「說吧,聖戰結束了沒?」
「你說審訊,嗯,結束了。」我克制著不讓視線溜回窗外。「我讀高中也三年了──東洲不可能和西爾帕差太多。」
塔克嗤之以鼻。「東洲絕不同於他校,妳明天就知道了。」
似乎只有塔克不認為東洲是好學校。我媽相信新學校是好事、我的治療師強調我在該校會表現更好、我爸說東洲不錯,但聽來像是我媽威脅他說好話,如果他人在家裡、不在非洲,他就會告訴我他真正的想法。
「總之,」塔克說:「平日夜裡的慘況仍不及週末夜。」
看得出來。現在是十點半,這地方一片死寂。我口中的死寂,相當於印第安那州郊外負鼠的總數。塔克該訓練我夜班的工作,因為暑期我只值日班──這是治療師的主張,並獲得我媽的加持。但學校即將開學,我們都認同我可以上夜班。
我拿起費尼根收銀機後面的神奇八號球,拇指滑向球身背面、用力摩擦,想抹去紅色的刮痕,我無聊常這麼做。塔克現在忙著排胡椒罐騎兵和對立的鹽罐步兵。
「餐館仍有散客。」他表示。「一些詭異的夜貓子。有一次我們遇到醉醺醺的男客人──你記得嗎,葛司?」
一縷煙裊裊穿越點餐窗口、升上天花板。為了回答塔克的問題,空中因而誕生幾朵積雲。我確定葛司的香菸不是真的,否則,我們已經違反上百條衛生法規。
這時塔克皺眉、沉著臉,以毫無起伏的聲音說:「噢,另外有位邁爾斯。」
「哪位邁爾斯?」
「他應該快到了。」塔克斜眼看著他一手主導的調味料小戰爭。「他下班回家時會順路過來。他就交給妳了。」
我瞇眼。「可以說明為什麼將他交給我負責嗎?」
「到時妳就知道了。」塔克抬頭時,一對車頭燈照亮停車場。「他來啦。規則一:不要和直視他的眼睛。」
「幹嘛,他是猩猩嗎?這裡是演侏羅紀公園嗎?我會遭到攻擊嗎?」
塔克嚴肅地看了我一眼。「很有可能。」
一個和我們年齡相仿的青年進門。他穿著白色運動衫、配黑色牛仔褲,梅傑量販店的馬球衫垂掛在一手。如果他是邁爾斯,他沒給我多大的機會直視他的眼睛。他直接走到我負責區域的邊疆,背牆而坐。根據經驗,我知道那裡是店裡視野最好的位置,但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樣疑神疑鬼。
塔克倚著點餐窗口。「嘿,葛司。你準備好邁爾斯的老樣子嗎?」
當葛司遞出起司漢堡加薯條時,他香菸的煙霧亦在空中裊繞。塔克接過盤子、倒杯水,就將東西丟在櫃臺、我旁邊。
我嚇一跳,因為我發現邁爾斯越過眼鏡框緣看著我們。揉成一團的紙鈔已在餐桌邊。
「他有什麼毛病嗎?」我低聲問。「你知道的…像是精神方面的毛病?」
「他確實和我們不一樣。」塔克氣悶地丟下這句話,便回頭建構他的軍隊。
他不是共產黨員、他身上沒有竊聽器。妳不准查看桌子底下,白痴。他只是想吃飯的年輕人。
我上前時,邁爾斯垂下視線。
「嗨!」出聲招呼後,我立刻縮肩膀。活潑過頭了。我清了清喉嚨、掃視餐桌兩邊的窗戶。「呃,我是亞歷克斯、」我壓低聲音。「你的服務生。」然後放下食物和水。「還有什麼需要我幫你服務的嗎?」
「不了,謝謝。」他終於抬頭了。
我腦內多條突觸爆炸。他的眼睛。
這雙眼睛。
他的瞪視剝去我層層皮膚、當場釘住我。血液湧向我的臉、脖子、耳朵。他有一雙我見過最藍的眼睛。這雙眼睛不可能存在於世上。
我手心發癢想拿相機。我得拍下他、紀錄眼前的畫面。畢竟釋放龍蝦不是真的,藍眼也不是。我媽不曾提到他,不曾對治療師、我爸或任何人提起。他不可能真實存在。
我在心底尖聲咒詛費尼根,他禁止我帶相機上班,因為我對一名戴眼罩、單腿為義肢的火爆男客人拍照。
邁爾斯以食指將那團紙鈔推給我。「不用找錢。」他喃喃道。
我抓著紙鈔衝回櫃臺。
「嗨!」塔克尖聲模仿。
「閉嘴啦,我的聲音才沒那樣。」
「他竟沒啃掉妳的頭。」
我將紙鈔塞進收銀機後,抖著手往後撥開頭髮。「是啊,」我說。「我也很意外。」
當塔克回後面休息時,我徵收了他的調味料大軍。葛司的煙飄上天花板,頓時被吸入通風口。牆壁擺動的風扇使員工佈告欄的紙張時起時落。
在我改造阿登戰役的途中,我搖晃費尼根的神奇八號球求解:德國鹽罐能否成功進攻。
稍後再詢問。
廢物。如果盟軍聽從八號球的建議,軸心國肯定戰勝。我全力克制自己不看邁爾斯,但我的眼睛最後還是飄向他,移也移不開。他動作僵硬地進食,像勉強自己塞食物到嘴裡,而且每隔幾秒就得推高滑下鼻梁的眼鏡。
我為他加水時,他沒動作。我盯著他頭頂黃沙色的頭髮、倒水,並以念力催促他抬頭。
我過於專心,沒發現水杯已經滿了,直到水溢出來。我驚慌地拋開水杯,結果水灑得他一身都是──他單邊的手臂、上衣到大腿。他動作迅速地站起來,卻一頭撞到上面的燈、桌子也跟著歪一邊。
「我──哦,要命,對不起──」我跑回櫃臺。塔克一手捂著嘴、一手拿著毛巾,臉脹紅地站在那。
邁爾斯拿梅傑的馬球衫吸水,可是他濕透了。
「我很抱歉。」當我伸手想幫他擦乾手臂時,我清楚意識到我的手抖個不停。
他躲開不讓我碰,他的視線一下看我、一下看毛巾,最後他推高眼鏡、抓著馬球衫逃了。
「沒關係。」他經過我身旁時低語。而後他完全不給我機會回話,直接走出大門。
當我清理完桌面,拖著沉重的腳步回櫃臺後,塔克鎮定地接過我手中的盤子。
「水啦,幹得好。」
「塔克。」
「請說?」
「閉嘴。」
他笑著消失在廚房。
那個男生是藍眼嗎?
我抓著神奇八號球、低頭看著球上的圓窗、摩擦刮痕。
現在最好先別告訴妳答案。
這個逃避現實的孬種。
還看不過癮嗎?快至書店購買吧www